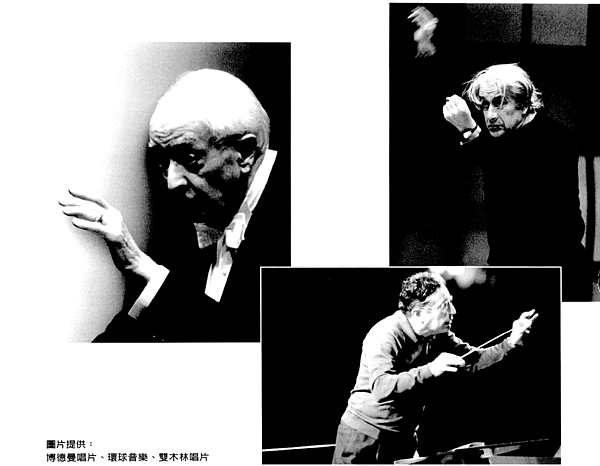
這次雜誌社一次送來三套由三位老大師指揮的布拉姆斯全輯,真是令人興奮又憂心。桑德林(Kurt Sanderling )、汪德( Gunter Wand )及柴利比達克(Sergiu Celibidache )三位大師都是出生在二十世紀初的人,除了桑德林的指揮生涯較為連續外,這三人的共同特點是越老行情越看漲。柴利比達克已作古,但EMI 及DG 卻搶發他的現場錄音。汪德則在RCA 的支持下,不斷的重複錄音發行布魯克納及布拉姆斯,大概已經破了重複錄音間隔的紀錄。而桑德林運氣稍差,缺乏五大唱片公司的全力支援,錄音散見各處,一直到最近才常以協奏曲指揮出現在Philips。
三位大師都不只一次發行過布拉姆斯(含海盜版),愛樂者或多或少都有其中幾個版本,而布拉姆斯的交響曲也是我家跨越千禧年的音樂。本來想用貝多芬的《 合唱》 揭開兩千年的序幕,但面對眾多的布拉姆斯,乃以號稱為「貝多芬第十號」的第一號交響曲做為迎接千禧年的大樂,選用了桑德林的版本,氣勢壯闊,撼動人心,特別在是第四樂章的終曲,令人不禁隨之揮舞指揮棒,深覺有為者亦若是。
淺論桑德林
桑德林在一九七二年與德勒斯登管絃樂團錄過一次布拉姆斯全集(Eurodisc / BMG ) ,這個版本一直是我心目中最佳的全集版本,也一直是英國留聲機雜誌的最佳全集推薦版本。桑德林的大半輩子是在共產世界度過,他曾跟穆拉汶斯基(Y. Mravinsky)一起指揮列寧格勒愛樂,也曾擔任過德勒斯登管絃樂團及位於東柏林的柏林交響樂團的總監,一直到年紀稍大,才逐漸在西方各大樂團游走。我曾於一九九二年在波士頓欣賞過他指揮波士頓交響樂團演出舒伯特的《偉大》 ,於一九九九年六月在阿姆斯特丹欣賞他指揮皇家大會堂管絃樂團演出蕭士塔高維契的《革命》 ,此時他已八十八歲了!他身體狀況保持良好,在波士頓時,虎虎生風,不下於年輕人,在阿姆斯特丹時,雖然必須坐著指揮,但還不至於太不便。
桑德林年紀大了以後,樂曲進行的速度變了,新的這版布拉姆斯全輯(Capriccio ) 就明顯的慢了些,而一九九九年現場的《 革命》 交響曲也是比一般慢。可是他又不像柴利比達克一樣的細嚼慢嚥,桑德林營造了一個開闊的音響世界,一個依然熱情如故的世界。桑德林只是「相對的慢」,而不是「絕對的慢」,每首交響曲大約比平均長了五、六分鐘,這樣的長度延伸,用於建構更雄偉的氣勢,毋寧是十分恰當的。
淺論汪德
汪德與桑德林同樣生於一九一二年,但這世界似乎一直到一九八○ 年代後,才突然發現有這樣一號人物。汪德現在儼然成為德奧系音樂最正統的代言人,舉凡貝多芬、布拉姆斯、布魯克納、舒伯特及舒曼,他的演奏都受到極高的評價。RCA 不斷的重複發行汪德的錄音,特別是布魯克納,已經搞不清楚現在最新發行的到底是那一版錄音了。如果檢視汪德的行程,曲目也多圍繞在三B 的身上。對一位已經八十八歲的指揮而言,演出的次數不多,曲目也不易擴展。在八○ 年代錄完第一輪的錄音後,RCA 似乎就跟著汪德的行程,開始發行現場實況錄音,從離漢堡很近的呂貝克(Lubeck )開始,到美國的芝加哥,再到睽違已久的柏林,再回到漢堡,汪德是三位同年齡大師中接受唱片發行最多的一位。
汪德在一九八二年與北德廣播交響樂團( NDR)發行過一次布拉姆斯的全集錄音,我將之視為最標準的詮釋。試想當時的NDR 跟柏林交響樂團、班貝格(Bamberg )交響樂團一樣,都流著最純正的德國血統,加上這位當時幾乎足不出戶的執著指揮,當然成就最標準的詮釋。RCA 現在再度發行汪德在一九九六年與NDR 的現場錄音,只比上一版略慢一兩分鐘,速度上的差異不大,詮釋上的差異也不太明顯,因此可以用錄音室的嚴謹與現場的緊湊,做為主要區隔。
淺論柴利比達克
至於同樣出生於一九一二年的柴利比達克,他雖然帶領過幾支廣播交響樂團,卻沒有接受正式的唱片發行。在淡出柏林愛樂後,他彷彿就消失了,一直到晚年回到慕尼黑愛樂,才又喚回全世界的矚目。但由於他極特殊的詮釋風格,各地的評論似乎都語帶保留,誠如他自己認為唯有到他音樂會現場聆聽才是最真的。然而對絕大多數的人而言,那畢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也就只那麼一次在台北的機緣而已。
因此,就柴利比達克的布拉姆斯而言,應該沒有那一個「版本」的問題,而只有那一場演出的問題。我手頭上有一套錄自一九五九年與義大利米蘭廣播交響樂團的海盜版全集(Cetra ) ,可以做為追蹤他演奏風格發展的起點。DG 搶得發行柴利比達克在司圖加特時代的錄音發行權後,率先推出布拉姆斯的全集,果然展現DG 驚人的轉錄功力,也讓人驚訝於這支南德廣播交響樂團(SWR ) 的功力。這版的錄音是在七○ 年代,也是柴利比達克重返德國的年代,顯然他與德國有著深刻的情感。EMI 也不甘示弱,整理出他在八○ 年代與慕尼黑愛樂的布拉姆斯全輯,此時,晚年柴氏獨特的風格表露無遺。然而EMI 的轉錄效果還是略遜DG 一疇。不過不論那一次演出,柴利比達克的音樂只能歸類為「樂迷俱樂部」型的收藏,跟伯恩斯坦的馬勒一樣,都有一群信徒,其他人都只能以崇敬的心卻語焉不詳的帶過。
淺論桑德林Capriccio 的錄音
桑德林這一套capriccio 的布拉姆斯全集,是跟柏林交響樂團錄於柏林的Christuskirche 教堂,時問是一九九○ 年,錄音效果非常飽滿溫暖,正好可以搭配此時桑德林所建構起來的宏偉建築。第一號交響曲經常是各大樂團放洋演奏時最愛演出的一首作品,一方面展現指揮及樂團的實力,一方面也讓觀眾感到音樂會內容及重量十足。桑德林的第一樂章速度特別慢,甚至比柴利比達克慢,但兩人的味道是不同的。柴利比達克往往是把樂譜分解,拿放大鏡抓出他認為該樂段最應突顯的特色,其結果常令人訝異於這首作品竟有如此之內在意義,但也常把我們熟知的行進方式攪亂了。桑德林則是比較純粹的動線拉長,所營造的是整體的氣勢,因此得到一個比較平衡的效果。桑德林的第一號呈現的是溫暖及宗教式的樂觀,幾處主題轉換時,採取了「留白」的停頓,以及終曲時不刻意加速,都很有東方宗教的味道。
第二號交響曲迥異於第一號的沈重,一開始就呈現了田園風,到第三樂章更成為如歌般的旋律。布拉姆斯在蘊釀許久後,才敢動手寫第一號交響曲,但在突破心理障礙後,一年後就交出第二號,心情輕鬆愉快,充份的在桑德林的演奏中展現。桑德林也刻意突出木管部份,因而更是風味十足,輕快順意,相當棒的一個演奏版本。
第三號交響曲跟第二號一樣,由於比較缺乏衝擊力,因此是較少演奏的曲目,但第三號可能是「最布拉姆斯」的交響曲,淡淡的第一樂章,令人思緒平靜。由木管帶出來的第二樂章,逐漸帶入內心深沈的一面。第三樂章由於被卡列拉斯填詞歌唱(收於「激情」專輯,Teldec ) ,可見其如歌般深情的描述。第四樂章則撩起帶有悲情色彩的激動,也是四首交響曲中唯一一首以緩慢的節奏收尾的交響曲。同樣的,這首是很合適桑德林風格的作品,他的表現足堪名列前茅。
第四號交響曲又恢復了激情及衝擊力,它有著更深刻的悲情性格,情緒不斷的被撥弄。它跟第一號所建構的宏偉壯闊不同,它是拼命的挖,挖到內心的深處,桑德林偏慢的速度,增添了悲劇的性格,像在終樂章,甚至有些華格納的味道跑出來了。這個樂章,桑德林的演奏比柴利比達克長,比汪德更多出兩分半鐘。因此,心情格外的沈重。
淺論汪德RCA 最新的錄音
汪德這一套新的布拉姆斯全集,是錄自他與漢堡北德廣播交響樂團從一九九五到一九九七年四次指揮演出的現場錄音剪接(非單場實況)。漢堡是布拉姆斯的故鄉,而汪德是以忠於原譜著稱,可預期這將是原味十足的版本。從第一號交響曲的第一樂章剛開始的定音鼓節奏,汪德就明顯的比桑德林快多了,快與慢並沒有好與不好的絕對差別,汪德從他一九八二年版到一九九六年版,在時問上最大的修正僅在第二樂章「持續的行板」,很難得的在新版上呈現出深情的一面,其餘時間相差無幾。第四樂章則以快慢速的交互搭配,近乎冷酷的表情,展現布拉姆斯巨大孤傲的身影,直接了當,毫不做作。
以汪德這種不放下身段或板著臉孔的詮釋方式,來到第二號交響曲這首布拉姆斯的「田園」,就顯得更加的嚴肅。汪德似乎無意讓樂團團員展現自己樂器的特色,而將這群樂手統一在一個強烈的意志及目標下,就像在德國北部常看到的德國人一樣,每個人都十分嚴肅,生活在極度自制的要求下。在桑德林手下是令人心曠神怡的春日田園,到汪德手下卻是秋風蕭瑟。
第三號交響曲在汪德的強烈意志下,我們幾乎是聽不到任何溫柔的輕語,即使是第三樂章的「稍快板」,卡列拉斯恐怕也唱不下去。然而樂團的水準實在很整齊,也充份展現德國人一絲不苟的特性。這首作品在汪德手下所達到的完成度,即便你覺得太重了,也不得不給予極高的評價,即使趕著交稿,也不忍按下停止鍵。
第四號交響曲是汪德新舊版本間,速度變慢最多的一首,但也不過才三分鐘不到。第一樂章「不很快的快板」似乎顯得放不開,太過於克制謹慎了,使得這個常叫人心碎的樂章欲言還止。但往後宛如倒吃甘蔗,汪德加上北德廣播交響樂團的音響,還是讓布拉姆斯這首最有特色及感情氾濫的作品活了起來,現場錄音的緊湊度的確吸引人。
淺論柴利比達克EMI 的錄音
EMI 出版的第三套柴利比達克與慕尼黑愛樂作品,包含了這一套布拉姆斯全集,時問分散在一九七九年到一九九一年之問,指揮家既無意進錄音室,這一套只能算是音樂會的拼湊全集。柴利比達克演奏的時間長度跟桑德林的新版是不相上下的,但味道卻是天南地北。第一號交響曲錄於一九八七年,打一開始柴利比達克就以很嚴肅的態度面對,而且有意標榜它的悲劇性格。第二樂章緩慢得令人心寒,桑德林只比柴利比達克多用了三十秒,卻覺得很勻稱莊嚴。第四樂章一開始的提琴撥奏部份,堪稱是標準的柴氏抽絲撥繭法,要樂團在那麼長的動線上堅持撐著,除非樂團與他有著充份的信任及依賴,否則必有一方棄守。我們的確可以從他的指揮下聽到很多不曾注意過的細節,但恐怕也因此而失去了此曲的全貌。
第二號交響曲錄於一九九一年,CD 解說中說這是柴利比達克晚年最喜愛及常演出的布拉姆斯作品。全曲除了第二樂章「不太快的慢板」太慢了外,進行的倒是出奇的順暢,像第四樂章就是少見的快意。柴利比達克固然以嚴肅的一面來看待布拉姆斯,但比起汪德那麼一板一眼的酷勁,柴利比達克的表情豐富多了。
第三號交響曲取自一九七九年,出奇快的第一樂章,幾乎無法令人相信此人是柴利比達克,而且音樂行進亦是順暢而不羈絆於細節。第二、三樂章則又恢復較慢的速度,一直到最後一個樂章才又來到正常的速度。整首交響曲呈現了柴利比達克少有的親和力及情感流露的一面,這也正是柴利比達克認為布拉姆斯在這首交響曲中所要呈現的。第四號交響曲取自一九八五年,跟第一號一樣,柴利比達克往布拉姆斯悲情的一面挖掘,但相較於第一號的變動性,這首作品演奏得較勻稱,特別到第四樂章最為精采,堅實有力又感情豐富。如果柴利比達克一直以這般較能為大眾接受的距離及樂於錄音,那至少在德國與卡拉揚形成南北抗衡,也可使得古典樂界多些活力。
結語
三位同年齡大師的三套布拉姆斯呈現三種完全不同的面貌,桑德林還是我的首選,無論是他所營造的寬宏架構及情感的自然流露,或是柏林交響樂團的演奏及錄音,這都是一套全方位的布拉姆斯,桑德林是被低估的大師。唯一的麻煩是這一套為四張高價位CD ,費用較高。汪德仍然是標準版的最佳選擇,北德人指揮北德的樂團演奏北德作曲家的作品,硬是被汪德的強固意志、冷峻表情控制在堅實的演奏下,是領略布拉姆斯的範本。至於柴利比達克,仍然是進階的版本,硬湊出來的全集,差異性頗大。如果再加上他在DG 的南德廣播交響樂團版本,甚至於cetra 海盜版的義大利時期,可以多些對大師軌跡的探尋。選DG 那一套可能是比較好的選擇,一致性較高。



 留言列表
留言列表


